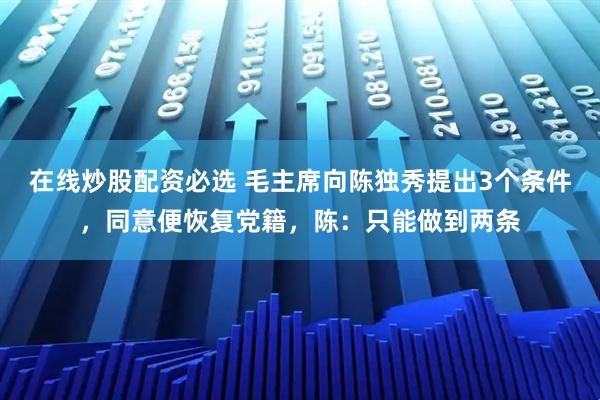
“1937年11月15日下午在线炒股配资必选,叶剑英一进门就压低嗓子说:‘中央有三个条件,请陈先生过目。’”话音落下,病中初愈的陈独秀微微抬头,目光既期待又警惕。那张写着三条意见的便笺,像烫手的火炭,改变了屋里原本沉闷的空气。
这是一间位于武汉江汉路的普通旅舍。陈独秀刚被提前释出,身体虚弱,却思维清醒。他扫了一眼纸条:支持中国共产党;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;承认托派立场错误。前三十秒,他没吭声;第Thirty-one秒,他摇头:“前两条没问题,第三条……我真做不到。”

门外风声呼啸,夹杂着江边汽笛。叶剑英没有多言,他清楚,眼前这位老人曾经统摄“新青年”风云,也曾在北洋政府监狱里熬过五个冬夏。若想一句话让他改旗易帜,谈何容易。叶把那张纸折好放回口袋,留了一句:“中央等您的回信。”他躬身告辞。
消息很快传到延安。毛主席翻着来信,沉吟良久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,主席对陈独秀既敬且惜。二十年前,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,捧着《新青年》彻夜不舍,那本杂志让他第一次意识到“神坛可以推倒,旧文法可以革新”。他后来说,“若无《新青年》,我恐怕还在读旧八股”。那句话不是恭维,而是真心。
正因如此,当1920年夏天毛泽东赴上海拜访陈独秀,两人几乎谈了整夜。马克思主义、俄国革命、湖南工运……话题一个接一个。毛泽东曾回忆:“那是我人生最关键的几小时。”然而短短七年后,两人却隔着国共合作与托派之争,分道扬镳。

造成裂痕的起点,要从大革命失败说起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政变,蒋介石挥刀反共,陈独秀痛失长子陈延年,却仍被责以“右倾机会”之名。共产国际电报雪片般飞来,要求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,从汪精卫那里“寻求突破”。陈独秀不同意,他写信给中央:“再留,犹如自缚。”结果,他被撤职,旋即被定性为“机会主义头子”。从此,他的政治轨迹进入阴影区。
更沉重的打击在1932年。陈独秀被租界巡捕逮捕,判十三年。狱中环境恶劣,他靠《史记》《资本论》度日,有时也写英文信,与狱外友人讨论西方工团运动。托洛茨基被流放阿拉木图的那年,陈独秀在上海孤灯之下,算是精神“并肩”。长期孤立让他对斯大林模式愈发警惕,对共产国际愈发失望。直到抗战爆发,国共再度合作,他才迎来“请君出狱”的机会。

面对毛主席开出的三条,陈独秀为何拒绝最后一项?核心就在“托派”二字。在他眼里,这顶帽子并非简单政治标签,而是“思想良知”。他曾对友人说:“我可以赞同中共抗战路线,但不能诬托洛茨基为法西斯走狗。”这句话今天听来梗直,却在当年苏联肃反浪潮里格外刺耳。
然而,毛主席并非完全不同情。张国焘晚年回忆,主席私下对他说:“中国托派的根子不同于苏联,若能并肩抗战,历史自会评说。”可政治现实残酷。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,将苏联“反托”口径原封搬到延安,坚决否决为陈独秀平反。康生更将“日本间谍”罪名往陈独秀头上按,文件一出,争论戛然收场。
不得不说,如果当时中央只有毛主席一人拍板,陈独秀很可能重回党内。但延安不是“单声部”合唱。叶剑英无计可施,陈独秀也不愿再妥协。1938年春,他迁居四川江津青木关,潜心翻译《路德维希传》《唯物史观浅说》,偶尔在田埂边与农家聊天,谈文学,也谈时局。他写信给李济深:“此身已退,仍念天下苍生。”

蒋介石想拉拢他,派人携巨款劝其组党。“蒋杀我儿子,何来合作?”陈独秀冷面回绝。到1942年,他因误饮霉蚕豆花而中毒,病体无力再支撑严苛的高血压治疗,5月27日辞世。各方噩耗传来,延安发电表示哀悼,毛主席在七大讲话中再度肯定其“建立党之功”,并嘱咐安徽安庆政府照顾遗孤陈松年。这份惦念持续了四十年。
回头看那张写有三条条件的便笺,它最终没有换来陈独秀的签名。他选择保留对世界革命的独立思考,也承担与之相随的孤独与非议。1945年,延安整风已见成效,“左”倾主义退潮,人们渐渐明白,“绝对正确”的口号本身就暗藏风险。陈独秀却已无法听见。
后人争论依旧:若他当年答应第三条,会否走入另一种人生?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。可以确认的是,在那场关系民族存亡的艰苦抗战里,毛主席需要广泛统一战线,陈独秀则更看重思想独立与批判精神。两种诉求,彼此尊重,却难以完全契合。历史由此拐弯。

有意思的是,1962年毛主席重读《新青年》手稿,对身边工作人员说:“彼时风雷激荡,一本杂志挑起千钧担。”若深究,那千钧担的一半作者正是陈独秀。一个革命导师,一个革命调度者,前后数十年,互为镜像又互作注脚。人事变迁,理念冲突,皆汇入时代急流中。
今天再谈“三个条件”,它们不再是政治谈判的冰冷条文,而像一面镜子,照见一个政党对早期领袖功过的复杂态度,也照见一个走到暮年的思想家对自我信念的执拗坚守。信念或许可变,坚守却难求。陈独秀说他只能做到两条,毛主席接受了这份遗憾。风云散尽,字纸犹存,曲终人散,各自无悔。
涌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