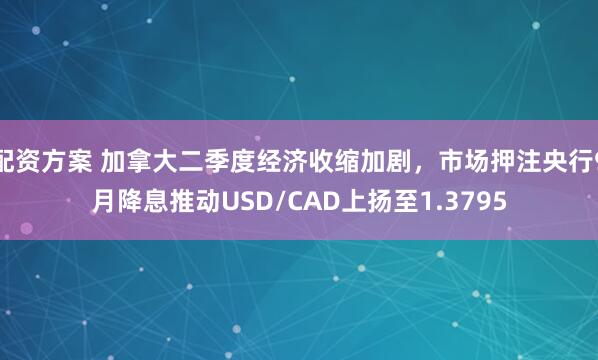【1947年3月18日,延安】“胡宗南要进攻了配资方案,你真打算丢下延安?”周恩来压低嗓子。毛泽东只把烟头按进烟灰缸:“舍一座城,换一个天下。”一句轻描淡写,却藏着对战局的通盘预估。料敌先机,这正是《三国》里诸葛亮给他的最早启示。

对诸葛亮,毛泽东既敬佩又挑剔。他反复向身边人强调:亮虽聪明,也有败笔;学他,别迷信他。也因此,他不满足于在纸上谈兵,而是把书页里的兵法拆开、重组,再塞进纷繁的现实。这种把古典智慧活化成现代战术的能力,使他在群雄逐鹿的年代屡屡转危为安。
读《三国》的种子很早就埋下。1906年,13岁的毛泽东坐在湘乡树荫里读线装本《三国演义》,别人还在识字,他已能讲出“隆中对”与“七擒孟获”的细节。母亲催他插秧,他往往回一句“等我合上这回书”。这种痴迷并非少年意气,一本小说从此成了他观察风云的参照系。

二十岁后的毛泽东进入湖南一师,研究的不再是情节,而是逻辑。他在读书笔记里写道:“用兵之要,在预见,在因势,在夺心。”这三句话后来贯穿他的大半生,而每一句都能在诸葛亮的行藏中找到影子。
先说预见。1916年,日俄签订“浦盐密约”,湖南师范的学生们议论无多,毛泽东却写信给好友萧子升:“二十年内,必有一战,不可不防。”二十一年后,卢沟桥炮声落地,预判成真。到了1934年,中央红军在湘江后只剩三万人,博古、李德坚持北上,他则斩钉截铁提出西进贵州。理由简单:敌强我弱,必须逆向思考。结果乌江突破,遵义得手,红军保住了脊梁。再到1947年,他放弃延安时抛下一句“少则一年,多则两年,我们还回来”,仅十三个月,西北野战军就打回宝塔山。连续三次大判断,没有“神机妙算”的神秘,只是把信息、地形与人心放在显微镜下反复推演。

然后是因势。诸葛亮借东风,不是天赐灵签,而是对气象的精密把握。1949年,华东、华中两路渡江部队原定四月中旬发动,毛泽东却连发电报催问水情。气象部门报告:五月江水猛涨,小船不稳。他立即拍板,把最后期限锁定4月20日。当天夜幕降下,江面风平浪静,四小时渡江结束,而国民党空军直到天亮也没明白为何解放军选了最难猜的一夜。试想若拖十日,长江主汛期来临,七千条木船极可能翻覆,战局就要改写。有人说他“等风”;更准确地讲,他是算风、选风,再借风。

夺心之术,最见分量。街亭失守,诸葛亮弹琴退司马;1948年冬,傅作义十万兵马偷袭西柏坡,情景如出一辙。当时华北我军主力全部在外,石家庄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空城”。汪东兴紧急调防,朱德电令二兵团南援,但真正把傅作义逼回去的,不是临时拼凑的几千守军,而是毛泽东对媒体战的精通。他连发三篇新华社通讯,逐条点出敌军番号与行军路线,“蒋傅匪军欲趁夜袭石门,殊不知我已布成天罗”。傅作义越看越心惊:对方掌握得如此详细,必有埋伏。他在保定以北反复徘徊,终究收兵。西柏坡的军号没吹,空城计却奏效,把十万大军挡在百里之外。
有人好奇,毛泽东究竟是否“照着《三国》打仗”?他自己回答得干脆:本本不能照抄,但精义必须吃透。“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”,这句玩笑背后是高度的实践能力。红军时期,他未曾通读《孙子兵法》,却从《三国演义》中借来信息主导权的概念;延安时期,他补上孙子的缺课,将“势”“奇”“正”融入整套作战体系;建国后,他让军委情报部专门把古代兵书与现代情报学对比研究。诸葛亮不过是他工具箱里的一把钥匙,真正的核心,是把钥匙插进现实这把锁上。

不得不说,诸葛亮留给后人的是案例,而毛泽东带给部队的,则是方法。他反复告诫年轻军官:先学会提问题,再去翻书找答案。正因如此,三次“料事如神”的胜利成了活教材——学兵书可以,但绝不能让兵书牵着鼻子走。
1958年庐山会议间隙,他在茶厅谈起诸葛亮,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:“亮有两难:其一用人不广,其二不敢犯错。若能放开手脚,未必只守蜀中。”说罢哈哈一笑,“咱们犯过错,也就学到这条。”在场者听得出来,他仍把三国当镜子,却时时提醒自己别被镜子里的影子束缚。

回头梳理这三件事——预见趋势、顺势而为、夺取人心——本质上是一条主线:掌握主动权。诸葛亮审时度势,毛泽东将之拓展成适用于现代战争的系统工艺;从史书到战场,从字里行间到枪林弹雨,他做到了“知而能行”。这才是诸葛亮留给后世最重要的财富,也是毛泽东真正借来的计谋。
涌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